
《花樣年華》2000
WHEN WE TALK ABOUT NEW LANGUAGE
與喘著氣的人力車夫擦肩而過,頭上懸著大大小小晃動的招牌,棉布長袍隨著匆促步伐泛起皺褶,來到人頭湧湧的拐角處,不是賣豆漿油條的老店,而是擺著新鮮出爐《禮拜六》的中華圖書館。每逢星期六,上海的書店門還未開,已有一群秀髮燙得油亮的都市婦女在守候,急著買這本輕薄玲瓏的周刊,想追看痴男怨女的峰迴愛情路。
民國初年的文壇捲起一陣新風,知識分子伏於書案上,琢磨著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來創作。他們銳意剷起舊土,沒料到卻讓鴛鴦蝴蝶派、禮拜六派這些野草種籽發芽生根。專寫才子佳人的哀怨情仇,試問又擔起救國救民的重任?偏偏卻是這些「庸脂俗粉」,最能討得大眾讀者的歡心,就連魯迅先生的母親也是鴛鴦蝴蝶派作家張恨水的忠實粉絲,常囑託兒子買新出版的小說。
改革從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靠文人高高在上的勸世宣言就可成就。常被詬病為靡靡之音的鴛鴦蝴蝶小說,不外乎寫歌女在動盪時代下的戀曲,或是京劇男旦被軍閥殘害而自殺的悲劇,除了賺取女子落在繡花紗帕上的熱淚,也意外讓白話文真正走入社會生活。這類通俗言情小說,白話中夾雜著古雅文言,題材意識上又未能提倡民主科學、痛斥時弊,半新不舊的模樣,就好像仍然纏著小腳的女兒家,剛從覆亡的晚清走出來般。但是,新與舊又何曾有一條明確的界線,可以一夜之間就徹底跨越?
常說語言為思想的載體,時值皇朝傾覆、西風東漸的新世紀,衣飾也何嘗不是尋常無聲的語言?由寬袍大袖到婀娜修身,旗袍的嬗變慢慢發生,一幅幅裹身的長布在剪刀裁衣聲裏,印證思想變化的激盪。
旗袍自滿清旗裝而來,清末的女伶就已流行男裝女着。到了女權覺醒的民初,女性為了追求與男性平等,一心摒棄所有女性化特徵,張愛玲在《更衣記》寫道:「五族共和之後,全國婦女突然一致採用旗袍,倒不是為了效忠於清朝,提倡復辟運動,而是因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就是這樣,連旗族女子都嫌「缺乏女性美」的旗袍,一下子受到漢人女子青睞。張愛玲用「嚴冷方正」來形容當時的旗袍,恰切地表達了那份偏執又決絕的平權理想,也令人想起最初倡議用白話文的文人一樣,一心只想破舊立新。
如我們所知,旗袍沒有一直以嚴冷方正的面貌流傳,在性別解放的思潮下,女性也不只追求看起來與男性一樣,在二十年代 FLAPPER 風尚影響之下,有的女子更穿起裁短及膝的旗袍,露出絲襪與高跟鞋,大膽又佻皮,好像隨時會笑著跳舞倒進你的懷裏。為了方便走動,旗袍漸漸有了開衩設計,不想那麼性感,也有裁成立體波浪邊的款式;後來又有人覺得立領不適合炎夏,掀起「廢領」的熱潮,影星梁賽珍就曾穿過一字領的旗袍留倩影。
在二、三十年代,旗袍並非為了約束身體而存在,更不只有曲線玲瓏的一面。若你樂於坦胸露臂,自可訂製網眼透視的款式;喜愛東西交融的含蓄優雅,除了纖挑修腰的長裙,也有上身為傳統領式、下身為印花 A 字裙的設計。張曼玉在《花樣年華》的旗袍造型深入民心,其實在《阮玲玉》中扮演阮氏一角,她所穿的旗袍有不少幾何線條,也是參考了三十年代 ART DECO 風行中國的潮流。跟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文白雙語」並行一樣,旗袍在繼承傳統的同時亦不斷翻出新意。
不刻意去為新舊交替立下分界,不抗拒外來的思想文化,也不鄙棄自身的美學傳統,才有了這麼蓬勃多彩的衣裝風格,旗袍的花期才可以那麼長,那麼歷久常新。張愛玲一張著名照片,也就是穿著清裝大襖所拍,為求上鏡一點,她又在外面加上浴衣,就好像她作品中的男女也活在封建與摩登之間,寫得既有鴛鴦蝴蝶的針法輪廓,內裏卻縫入了現代的精神。語言或時裝,都無法強求一夜之間的革新,所有翻天覆地的改變,你回過頭去看,原來都如豐子愷所寫的「漸」,一天一天、一時一時、一分一分、一秒一秒地,圓滑而緩慢地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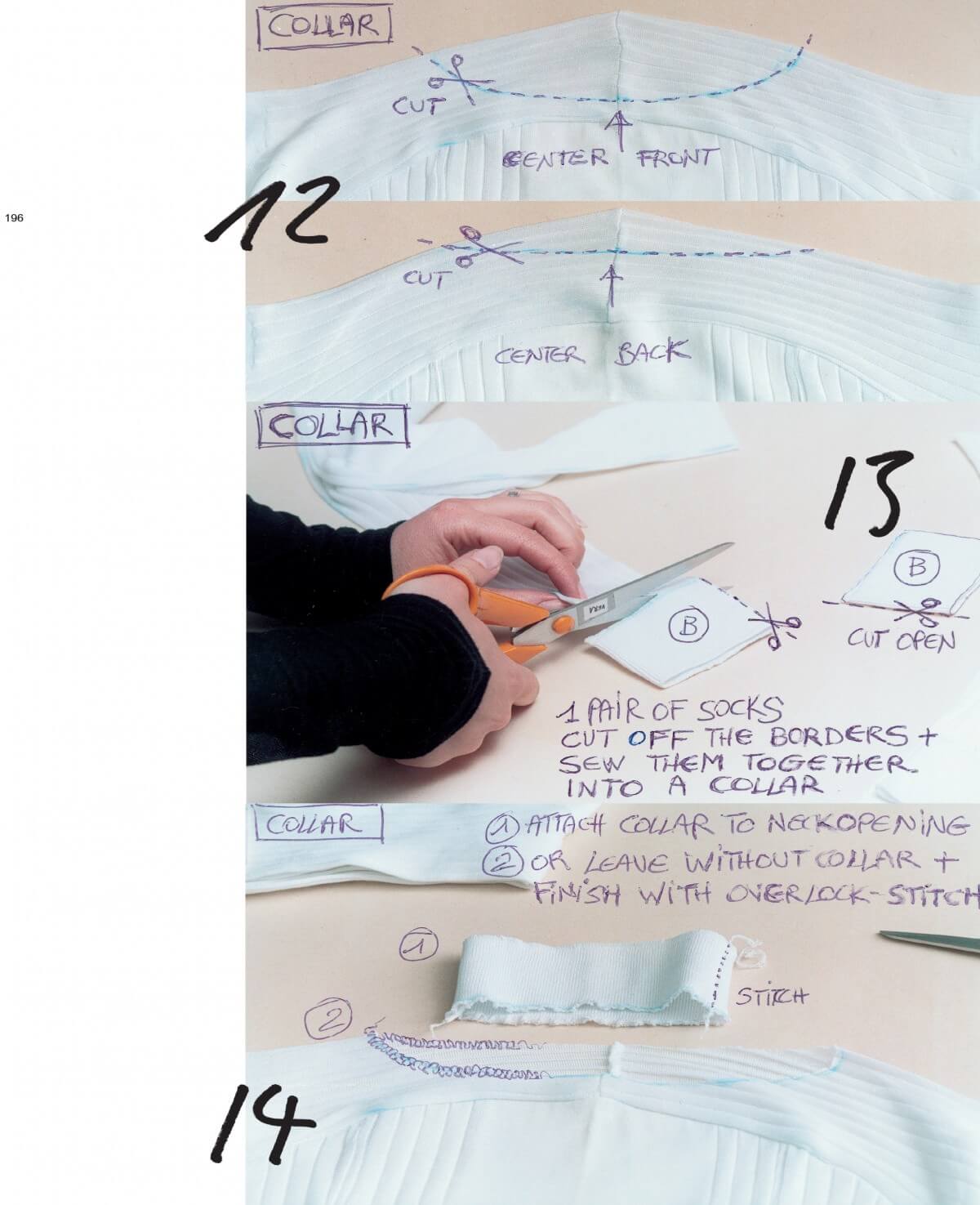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