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記得二零二二年的最後一天?」在紙皮箱裡面,和光抱著腿問。
我知道她問,並不是因為忘記。
「去了 LANDS END,撿了一塊石頭,用塗改液寫上年月日,丟了入大西洋。」
「兩年前呢?」
「在白金漢宮向御林軍要求祝英女王新年快樂被拒。」
「後來英女王死了。」
「妳收集的九十六個女王頭硬幣還在枕頭底呢。」
她皺著眉頭笑,像個不記得把玩具亂丟到哪裡的孩子。
我便也笑起來:「不要問我為甚麼會在枕頭底哦。」
和光向來有種「告別癖」,無論任何事情終結,都會要求有個鄭重到近乎神聖的告別。於是,在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我們從倫敦伊靈出發,於三十一日夜來到香港上環,向某個慈祥的老婆婆買來兩個紙皮箱,在那家我們要告別的書店外找到一片有街燈如 SPOTLIGHT 映照的地方坐下。

紙皮箱大得很,我坐一個,她坐一個,像兩隻等待領養的狗。
往中環方向走半段路是蘭桂坊;再繼續往前走,就走不動了。幸而慶祝新年的人潮還沒漲到這邊,頂多就是間中走過三三兩兩,像浪花濺出水。幾個英國少年看見我們,嚷著要把我們封箱搬回國。他們以為這是販賣人口,但對我們來說,其實只是早幾個小時回家。
我們將會乘坐一月一日上午十一點四十八分的飛機離港。
我沒有和光的告別癖,按理不應該附和她這種——我想多數人會稱之為「唔抵」的——行為。多數人會說,首先為了告別一家書店而飛越半個地球就不是很抵,而就算基於某種個人理由而非這樣做不可,也應該搭單做其他事,比如搭單食雲吞麵,搭單逛西九 M+,或者搭單探望偶爾會給你的 IG 貼文心心但已經多年未見的朋友,而不必僅僅待個十六小時就走。
可是「搭單」的意思不就是這些事情都不能成為主菜嗎?而想到這裡你就會發現,其實就算你多麼想食雲吞麵、多麼想去西九、多麼想見朋友,退一步說,怎麼都沒有所謂。
退一步說怎麼都沒有所謂——有時我覺得人世間所有的事情都是這個樣子。
這大概就是為甚麼,許多次許多次,我都已經向領班請好假,但當我即將要在 LHR <-> HKG 的購票頁面點 CONFIRM,結果都是把瀏覽器關掉。
「你就是這樣的人。」和光嘆氣。「這次的機票,我買。」
「OK。」我說。她比我更了解我自己。「沒所謂。」
和光抓住紙皮箱的邊緣,讓自己坐直一點。她的指尖在 GOOGLE MAP 上比劃。「從上環站開始走,走這條路。這裡轉彎,這裡再轉⋯⋯然後,呵。」她抬頭看我,朝地面點兩下。「便來到這裡。」
「總是走這條路?」
「人在歸屬的地方總會不其然走同一條路,因為路成為了身體的一部分。」
「這是心理學理論?」
「文學。」她說。「然後買書。接下來這樣走。這樣--喝!便去到你那裡。」
「總是走這條路?」
她向我微微一笑。
四年前我還在這附近有一家小酒吧。吵鬧的客人被我全部趕走後,剩下來的就好像一部部無聲的黑膠唱機,沉默而古老。和光是絕無僅有的年輕人。那時候的她正值大學畢業之後、投身社會之前,總是一個人,挾著一本書,點一杯熱麥精 BAILEY’S 呷著讀。某個不好賣的作家的詩集,某個破產藝術家的畫冊,某個找不到教席的學者的電影研究論著。這些書,她說,都是在那家書店買的。
我說我知道那家書店,它的老闆娘曾經在 IG 找我講過話。
「啊。」在吧枱邊,她身體探前。「你是個作家?」
「原意是想辦一個市場推廣帳戶。」
「後來呢?」
「成了市場驅趕。」
她吃吃地笑起來。「沒那麼壞吧,最少那書店的老闆娘會接觸你。」
「可以算作成就?」
「她很厲害噢。」
「外星人很厲害,不代表他們抓去解剖的地球人也很厲害。順帶一提,那個IG到現在還沒能儲到一百個追隨者,連普通人的普通朋友數字都不到。」
「我也沒有一百個朋友。」
「有多少?」
她點出自己的 IG 頁面。我成為了她的第九十九個朋友,和第一個男朋友。
*
自希斯路機場起飛一小時後,她把我戴在頭上的耳機拉下來。
「噯,到了書店我們要做甚麼?」
於是在餘下的航程,我們構思各種各樣告別一家書店可做的事:圍繞社區走一圈、在毗鄰的餐廳吃飯、拍下書店的每個角落……後來思想則按和光一貫的作風開始脫韁:買清潔用品洗刷書店外牆、裝偷聽器收集書店環境音、將二零二三年的第一線晨曦抓起來,送進書店郵箱。
「無論如何,書是一定要買的。」她說。
這是一百二十七個構思裡面最可行的一個。
而那時候我們都不知道書店會在六點半關門。
「如果有買到書,現在就可以看了。」我看著已經打烊九小時的書店慨嘆。
和光便忽像想到甚麼似地,起身往街口走去,一會兒後又搬回一個紙箱。她把那紙箱拆了,用唇膏在紙皮上畫寫。寫好後自豪地給我看,那是一句桃紅色的話。
強烈反對關門
「好像有點不太對。」
「哪裡不對?」
「煽動民眾情緒?」
她思索一會,在句末添了兩點和一撇,然後把標語整齊地橫放在我們面前。
強烈反對關門 🙂
*
我在我那人跡罕至的 IG 曾經寫過一個故事。故事的第一段引述歷史學家說,所有人都不過是時間長河裡面的一顆細沙;第二段描述一隻加拿大灰熊抓三文魚;第三段寫牠巨掌一揮,許多沙子便連同三文魚濺到岸上去;沒有第四段。
和光在貼文下留言:「市場驅趕。」
後來我在酒吧問她怎樣想。
「你喜歡這個故事?」她反問我。
「喜歡啊。」
「那給你畫一隻灰熊當插圖。」
貼文的附圖原本是《國家地理雜誌》的照片。換上和光的插畫後,點擊率提高了 3,或300%。
*
「其實我知道我們要幹甚麼。」天色開始從黧黑轉湛藍的時候,她終於說。
「寫告別語。」
「我們又不是書店代表。」
她搖頭。「你的 IG。」
「都關這麼久了。」
「雖然我有點晚,但還是可以寫的。也應該寫。」她堅持。
「寫了沒地方發,發了也沒有人看。」
「31-12-2022 丟進大西洋沒人知道;我們坐在這裡也沒人注意。不是?」
「我只是覺得沒所謂。」
「那甚麼才有所謂?」
我沒有說出口,但她知道我怎麼想,如是便顯得有點悲傷。
「有所謂的。就算人總有一死,這也不等於我們不需要好好葬殮逝去的人,因為所有的告別都是一個起點,如果沒能懷著安定的心好好結束,所有的事情都不會能夠安定地好好開始。」
和光常說和我在一起總好似住在空中樓閣,而我,其實亦承認。只是我不知道為甚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現在已經二零二四了,可有時我覺得你根本是活在另一個時空。」她問我:「在你的世界,現在是哪年哪月?」
哪年哪月呢?
「來。」她溫柔地抓起我的手。「沒關係的,我們可以一起寫。」
我的嘴巴輕微顫抖。
*
後來我有好幾次想,如果那時候我選擇寫,和光會不會和我坐同一班機回倫敦。
然而這恐怕是不可能的,最少有兩個層次的不可能﹕首先,我不可能有足夠勇氣去寫;其次,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和光,早在買回程機票的時候,已經給自己買了另一張。
人們說離開是為了回來,我們回來是為了離開。
二零二三年離開,新的一年就此開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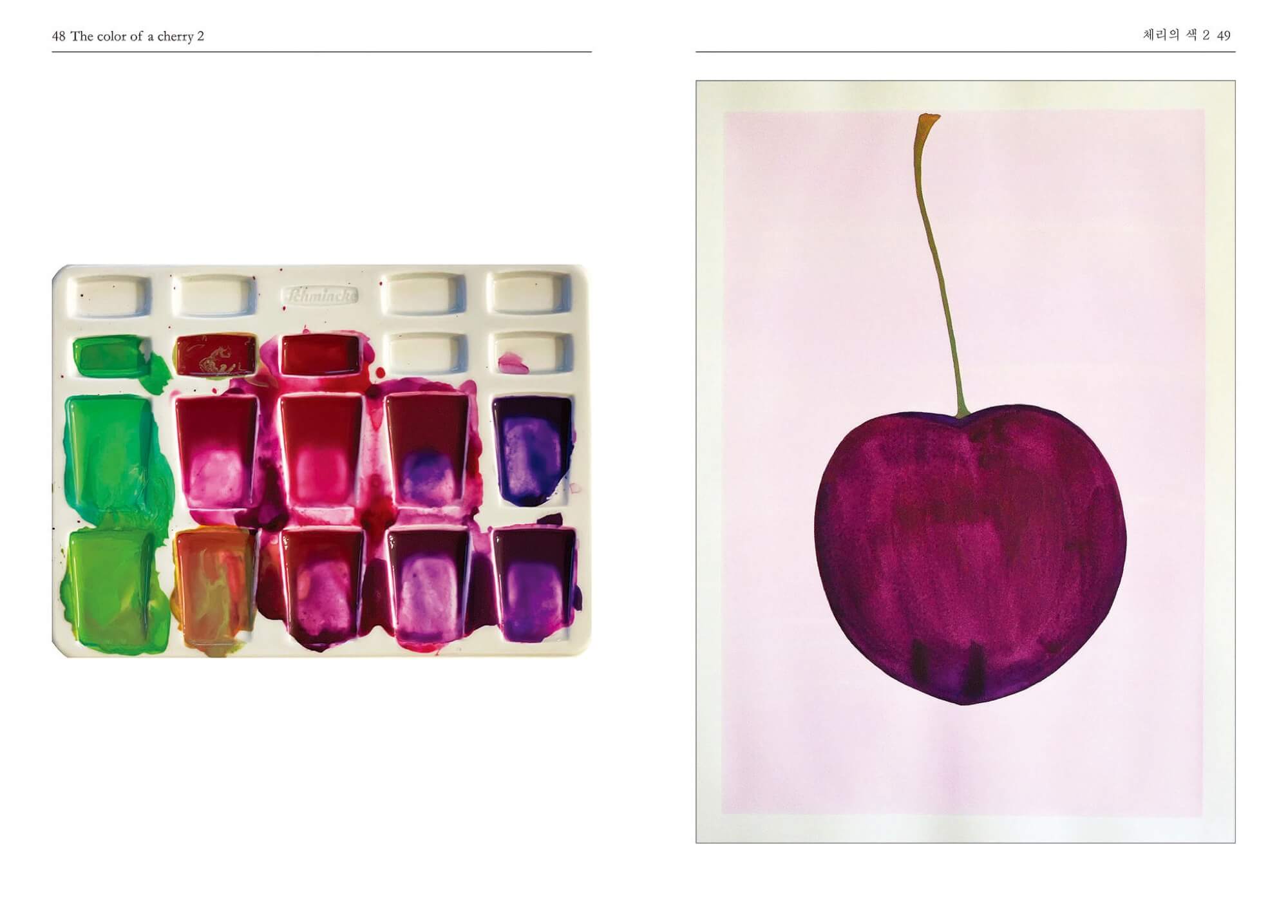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