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尤清早五點半出門的時候妻子還沒起床。一般來說他都不會在妻子起床前起床,以避免弄醒她帶來的麻煩。只是今天他必須要在八點到九點之間抵達 F 公司的轉運站,而倫敦的高速公路在高峰時間,基本上是停止運作的。
「嘖。這麼早幹嘛?我不用上班了?」
「得去取馬桶。」阿尤告訴妻子。
儘管昨天已經確認七次,但阿尤還是再次打開 GOOGLE MAP,輸入物流公司 F 的地址,查看他要怎樣走到巴士站,怎樣坐巴士,怎樣在那個連名字都沒有聽過的地方下車,再步行到目的地。
阿尤的馬桶就在那裡。
馬桶是十天前訂的。當時他和妻子剛搬進這個新居,發現馬桶漏水嚴重,沖水時廢水會像射水槍那樣飛濺出來。請來水喉工,水喉工證實了馬桶的死亡。在有新馬桶前,他們只能去一點三公里外的麥當勞。「每次上洗手間都要來回二點六公里。」妻子不滿。「我將因此練得健步如飛。」所以阿尤訂了一個聲稱可以在翌日下午六點前送達的馬桶。但第二天馬桶沒到。阿尤問店家,店家叫他問 F 公司。阿尤上 F 公司的網站安排第二天再送。還是沒有送到。他填寫「聯絡我們」表格請他們第二天再把馬桶送來。還是沒有。他又用即時聊天系統,這次獲得 F 公司的聊天機械人說會在七十二小時內跟進。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到第五天,F 公司回覆說對阿尤遇到的問題深感抱歉。F 公司表示,阿尤是次體驗並不是F公司想要給予客户的,他們已經安排馬桶在第二天的六點前送達。沒有。
「怎麼你買個馬桶都買成這個樣子?」妻子質疑。
阿尤發現他可以取消送貨,改為選擇到轉運站自取。去轉運站要轉三次車,單程一個半小時,雖然遠,但阿尤想,最少他可以保證馬桶到手。
天剛亮。四月的倫敦雖然已經算是入春,但天氣仍然寒冷。小路上的木凳、圍牆和燈柱都掛著水珠,每顆水珠都像一部小冷氣機。車站有一個白人,一個印度人,和一個黑人,阿尤與他們一一對望並點頭致意。與他們等巴士讓阿尤有一種安心的感覺,因為這讓他覺得自己在英國也是個有事幹的人。客户自取真不壞,他想。早就應該自取了。不過如果能夠送到家,就沒理由自取。F 公司也是跨國大企業,誰知會連個馬桶都送不到。
不過現在無所謂了,將馬桶搬回家,這事情今天就可以結案。
倒是不知馬桶有多重,搬不搬得動。搬不動還好,搬了,半路卻掉在地上碎掉就萬事皆休。也許可以坐 UBER,不過 UBER 是載客的,不知道載馬桶是否合法。他也可以問司機,不過首先你得要召了 UBER 才有司機回答你。這是雞先與蛋先的問題,很多事情都是這樣,剛到英國的時候他就經歷過一次﹕有銀行帳户才可以租房子,但要有地址才可以開銀行帳户。
如果馬桶搬得動就不必為這種問題煩惱。二十年前,阿尤會覺得自己連阿爾卑斯山都搬得動,但現在他已經四十七歲了。
到達F公司。看手錶,才早上七點。轉運站的大門還關著。那是一座像個大鐵皮箱的建築,位處一片空曠的工業用地,左邊是一家車房,右邊是另一家物流公司,背後則是一座不知生產甚麼的工廠。雖然時間尚早,但已經有一些送貨工開著印有F公司招牌的貨車進出貨倉。阿尤看見很多司機年紀跟他差不多。聽說在英國,貨車司機是高收入行業,這些人應該賺得不少。不會比阿尤在香港做買辦的時候多,不過肯定比他現在好。他現在失業,家裡財政由妻子一個人支撐。人還是很受物質條件影響的,自從妻子成為賺錢的那一位,她的口氣便改變了。可以的話他也不想辭工離港,但為了孩子的教育,不得不走。再者,香港這地方真是待不下去了。

「早安,有甚麼可以幫到您?」一個女職員看見阿尤站在門前,有些訝異。
阿尤給她看手機上的送貨單。
女職員說:「我盡快為您處理。請到裡面等候。」
阿尤在接待處的沙發坐下。女職員進到裡面的辦公室,又在大約十分鐘後出來。
他以為她會帶著馬桶出來,但沒有。
「您的貨物已經在今天早上送出,傍晚六點前就會送到您家門口。」
這麼說馬桶就是在剛才其中一輛貨車上與阿尤擦肩而過了。他想問她為甚麼點了客户自取但馬桶還是會上車,但又覺得就算問了大概她也說不出個緣由,再者,這並不是一件壞事,最少他可以省卻自行搬回家的煩惱。
女職員有禮貌地說:「您可以留下電話號碼,回家靜候。有甚麼問題我們會打給您。」
「謝謝。」阿尤說。
他的妻子在家辦工,全神貫注在一個五顏六色的試算表,好一陣子後才注意到阿尤已經坐在電視機前。她問他馬桶在哪,他告訴她正在路上,六點前會到。
「一個家,終於有廁所。」他的妻子感嘆。對於這起事件為她帶來的不便,阿尤也覺得不好意思,不過他又能怎麼樣呢?
當等到晚上九點他們終於接受馬桶今天還是不會來的現實,妻子回答了他心裡的疑問。
「又不是第一天沒送到。知道它不會來就該一早把訂單取消,買另一家店。難道這一家壟斷了地球上所有馬桶?」
阿尤確實未曾想過取消訂單這一招。可是他想不通,如果要取消,應該在哪個時間點取消。總不能在訂了第二天就立即取消。還有一個問題是,如果第一個馬桶不來,他又如何能保證第二個馬桶會來?想來想去,這事情怎麼都不應該說成是他沒有取消訂單的錯。
「明天早上我再去一趟。」阿尤說。
而第二天,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同一個女職員以同樣有禮的語氣對阿尤說:「先生,您的貨物已經--」
--阿尤早就感覺到了。
「非常抱歉。」女職員說。
「不,不必道歉。這也不是妳的錯。」
「您可以留下電話號碼--」
「昨天已經留過了。順帶一提,送貨單上本來就有我的電話號碼。」
「⋯⋯抱歉。」
「我說了,這並不是妳的錯。妳只是被推出來向客户道歉和要電話號碼的人。」
「感謝您的理解。」
阿尤卻皺起眉頭。
「其實我不理解。」他說。「這到底是誰的錯?也許是送貨工,但又也許不是,他不過是按照系統指示把貨物塞進貨車再送到指定目的地而已。這麼說是系統工程師的錯?又很難這樣說,系統工程師不就是聽老闆的話寫寫程式?既然如此,是老闆的錯?是貴公司CEO的錯?對,可以說是CEO的錯,畢竟作為CEO,所有問題的終極責任都應該由他承擔。但要他因此受責難也很無辜,畢竟他可是連我買了個馬桶都不知道。」
「先生,我理解您對這件事感到不愉快,您提出的意見我們會向有關部門反映。」
阿尤點頭。然而他覺得自己並不是在提意見,而是在描述一種無力感--一齣悲劇正在他身上上演,他已經付出巨大的努力去阻止它,也願意付出更大的努力去阻止它,然而還是無法阻止它。而更令他感到絕望的是,這悲劇的發生,並不源於任何人的錯。他的追究沒有對象,憤怒沒有對象。他也不可以報仇。
「向有關部門反映了又怎樣?」
「有關部門會作適當跟進。」
阿尤看見接待處有一道牆寫道「你的觀點 我的進步」,每個字母都有他肚子那麼大。牆中央是一個意見箱,左邊還有一疊整齊放在公文匣的表格和一排削得尖到可以刺人的鉛筆。他就拿了表格和鉛筆,坐在沙發開始寫。一寫,阿尤就停不下來了。他從第一天沒能收到馬桶開始寫起,寫到今天第十二天。他也寫了沒有廁所的日子怎麼過,寫了他妻子的反應,甚至寫了自己失業,以至從香港移民到英國的原由。他寫呀寫呀寫,表格滿了就填下一張,鉛筆鈍了就拿下一枝,阿尤這輩子第一次寫這麼多字,也驚訝自己竟然這麼能寫。那封意見書竟然成了他的一本自傳。
「尤先生?」不知過了多久,女職員走近他,膽怯地打斷他的思路。
阿尤恍惚地看向女職員。由於目光過於渙散,她的臉與她那件印有F公司字樣的反光衣和胸前的職員證糊在一起,成了一幅潑墨似的抽象畫。
他用兩手食指擦拭眼睛。
這麼一擦,竟然豁然開朗了。
他看見一個新天地,透過一道通往天國的大門向他敞開。那裡有野花,有嫩草,有吹響喇叭的天使,散發靈光的上帝。他不再一籌莫展,因為那裡有著無限的可能。他好奇自己為甚麼從來沒有想過這些可能,明明他早就已經聽過許多人說,也見過許多人做。只是從前,他覺得這些事離他很遠。
他走到女職員身後,在接待處通往辦公室的玻璃門前,坐在地上。才剛坐下,就有一個男人想要進去辦公室,也有人想要從辦公室出來,但他們只能在阿尤的面前和背後停住腳步。「怎麼回事?」他們問。阿尤第一次慶幸自己中年發福,因為這讓他可以死死的把門擋住。
「先生,請您冷靜。」女職員說。
「去叫你們的送貨工回來。」
「先生,我們不能這樣做。」
「妳們當然不能。要是妳們能,我還用坐在這裡?」
「先生,我明白您現在非常憤怒,可我們實在沒有辦法⋯⋯我們的系統顯示,您的馬桶將會在今天內送達您家。」
「甚麼時候?」
「下午六點前。」
「他媽的下午六點前,六了幾百萬點!我要馬桶,現在!」
「我們真的沒有這樣的機制。」
「很好,你們肯定也沒有處理客人堵路的機制。」
「先生⋯⋯」

她還在嘗試說服他,但四個穿著藍色保安制服的大漢已經推門進來。這些大漢一個個凶神惡煞,二話不說就朝阿尤擒抱。但阿尤知道怎樣做,他早就在電視見過這樣的場面。他交叉兩手,穩坐如山。他覺得自己就像坐在一艘巨輪的船首,在一面閃著金光的大洋上航行。在這裡,他不怕風,不怕浪,不怕物流公司,不怕妻子。他覺得自己是個勇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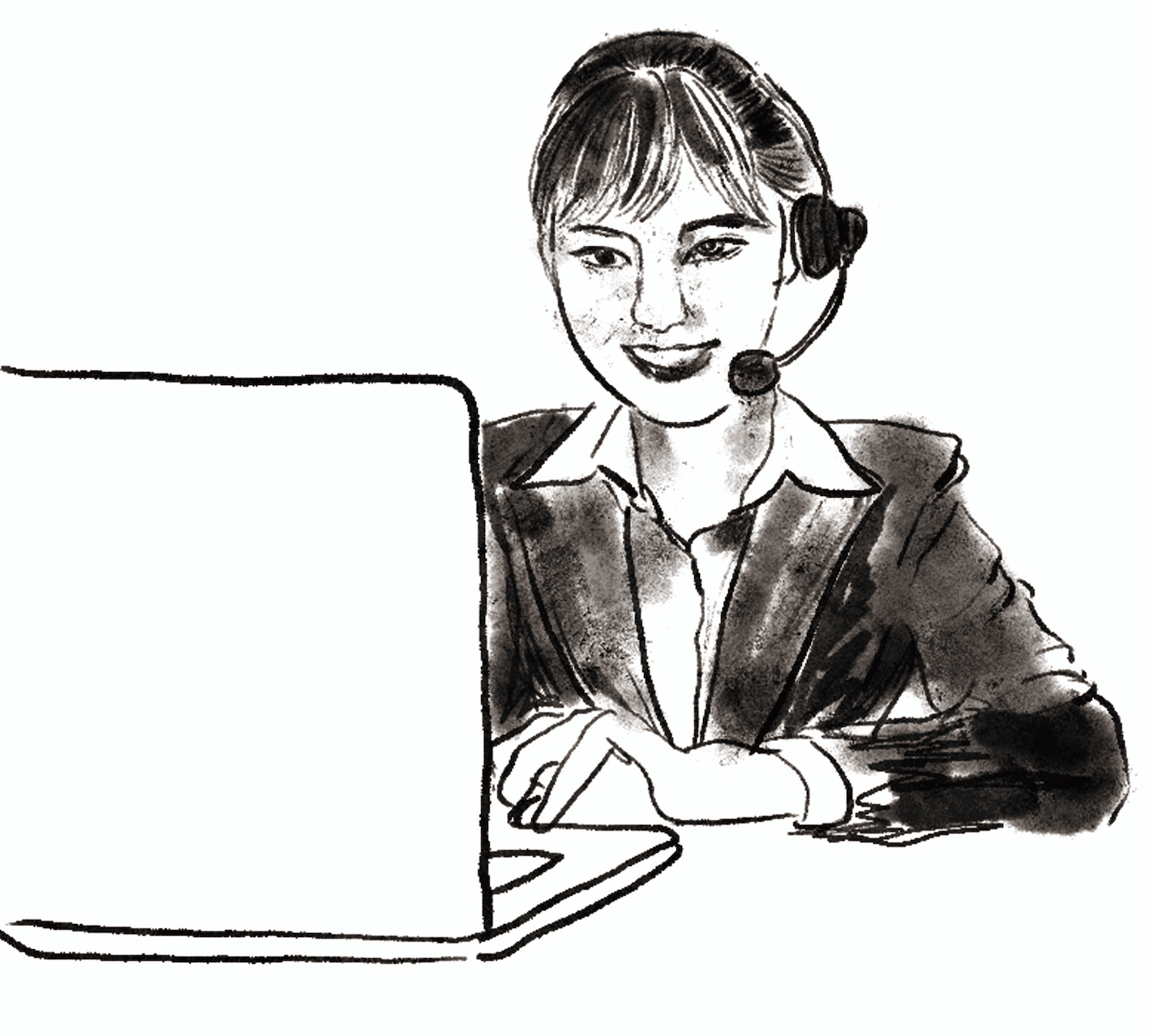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