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我來說夢想只是一個背包的重量,
於是我放下眼前資本主義的腐敗生活,追夢去,
晚機飛越印度洋,再從埃塞俄比亞轉機到達納米比亞,
我明白要看美景前總要勞其筋骨,但接近二十小時的飛行,
對年近六十的我有點過分,是一種折磨。
為了要見與世隔絕的辛巴族紅泥人,
一路上受罪不少,
下機後還要坐六小時的吉普車,
炙熱的陽光,滾滾的沙塵,
車子不停地顛簸在土路上,
到埗後全身落滿塵埃。


一進村,我的眼球被一個個裸露上身,
棕紅色的土著搶奪過去,
心情一下子澎湃起來,
她們渾身塗上了紅色麵糊,
麵糊用牛油、赭石和草料混合而成,
她們深信這樣能抵禦暴曬,防止蚊蟲叮咬,
更重要是令她們更具魅力,
不同年齡的女子,髪型和飾物有很大區別,
未成年的只能梳兩條小辮,
成年的梳多條辮子,腿上還會穿上串珠,
已婚的頭頂繫上小羊皮蝴蝶結,
胸前戴上海螺代表已生育,
身上飾物愈多地位愈高,
因為水源短缺,紅泥人不洗澡,
改用傳統美容術,紅泥塗抹全身,
還用香薰沐浴保持自身清潔,
她們把熏燒的木炭放在一個碗中,
等待煙慢慢擴散,以煙所產生的芳香自我淨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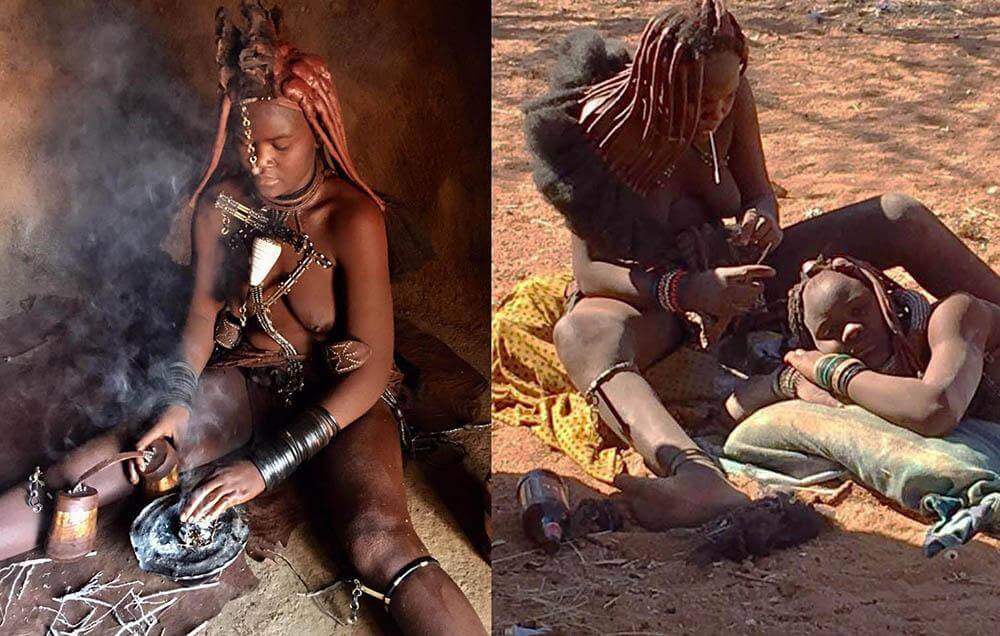

當香港設計師遇上土著設計師,
當大部分紅泥人懶洋洋正在曬太陽,
我看見一紅泥女子專注地工作,
她正在用鴕鳥蛋殼編織着手帶,
這種手工藝,在JCCAC市集,她是文青,
在巴黎時裝周,她是Haute Couturier,
在這?她只是一個平凡的婦女,做點手飾賺取外快,
她擁有系列,不用加上品牌,
作品毋須宣傳,就在地上發表,
隔着iPhone的熒幕,
我們互相對視,
她黑亮的眼睛裏,沒有不安,沒有焦躁,
只灑出了對我的好奇,
她微微地抬起頭,移動身子,
抖落一地鈄陽。

整天紅沙紅土紅泥人,
回到旅館我染紅了眼晴,
看什麼都是紅的,
旅館主人問我作為設計師,是否來找靈感,
我無言以對,
此時我想起1997年John Galliano為Dior而設計的非洲系列,
我不知道Galliano有沒有來過紅泥人村,
從網上看到他的設計,模特身上掛着光彩艷麗的配飾,
再看看手機拍下來紅泥人飾物所留下歲月的痕迹,
我知道,我對時尚有了新的認識,
時尚從來不是踏着優雅而來,
時尚更是對文化的一種誤讀,
正因為這種誤讀,人們從中尋獲了他們所要的文明優越感。









Comments